
起点
没有谁,比斯宾诺莎的哲学更令人充满激情;也没有谁比斯宾诺莎更容易引发互不相同的解读。对于其同时代人而言,斯宾诺莎被视为一个无神论者,一位亵渎神和神人共弃的人。

斯宾诺莎哲学之起点,实际上源自于中世纪时期关于爱的理论:“一切朝向有生有灭的事物的爱,都会导向各种激情:快乐、痛苦、忧伤;但是,朝向某种永恒的、无限的事物的爱,带来的是某种的纯粹的快乐、某种免于一切忧伤的快乐”。在中世纪时期,人们发展了关于爱的理论,关于人间一切的人或者物的爱,都是短暂的,都是引向激情与毁灭。唯有去爱那永恒的东西,才会有永恒的爱,而唯有上帝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永恒的东西。斯宾诺莎不同于这些基督教的地方在于,从一套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方式来言说这种爱:“爱基于认识”。
这种认识,又基于笛卡尔式的方法。数学和物理学,已经证明了,人的理性具有一种能力,能够发现或者认知到清楚明白的观念,并且用确定的方法将这些观念连接起来,从而显现出理性的不断扩展甚至没有边界的能力。斯宾诺莎是笛卡尔主义者,还在于他认为,通过对感性事物的认识,不可能逐步上升的方式,提高到理性认识,相反,只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一下子进入到理性认识之中,这就是《伦理学》中所说的第三种认识(直观)。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的第一种认识,就是感性认识,包括经验认识和通过阅读和听闻获得的知识;第二种认识,则是知性认识,通过推理获得的知识;第三种认识,则是通过直观获得,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最根本的一些原则的认识,这些认识并非通过感性获得,也不是通过推论而得,只能是某种直观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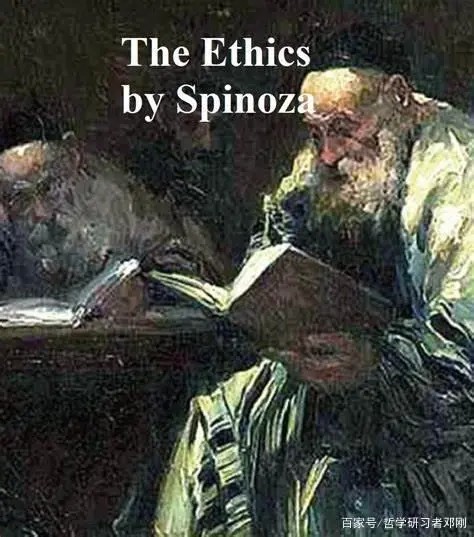
认识神
知性的原则之一,在于“肯定观念要先于否定观念”。一切肯定都是否定,因此,最完美的肯定性,就是神的观念。笛卡尔曾经把思维和广延视为相对实体,因为思维只是思维,也就是受限的,而真正的实体是不受限制的。
“广延是上帝的一种属性。”这句表述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从物质方面来设想神。但斯宾诺莎的说法需要结合笛卡尔的物理学来理解。对于知性而言,广延本身是无限的、不可分的;自然界的诸物体,不是广延的组成部分,而是构成对广延的限制。例如,在黑色的幕布上,绣上几颗黄色星星,这几颗星星并非幕布的组成部分,而是对幕布的某种限制。物体间的区分,不是实在的区分,而是样式的区分。
对于斯宾诺莎,实体与样式之间,并不是主体与述谓的关系,而是实体作为使得在每个属性之中的诸样式成为可能的原因。在所有的属性之中,都有着某个同一的基底,正是这个基底使得诸样式成为可能。神是万物的原因,神是实体,神也是自然(Deus sive natura)。
人的本性
人的精神应该致力于通过对事物的演绎,从而使得认识作用于抵达我们的善。神的属性,我们只认识两种,一种是广延,一种是思维。每种属性都是无限的,但人的本性,即人的灵魂和身体,使我们处在有限之中。从流变中如何能生出永恒?这个问题是一切从柏拉图主义出来的哲学所面临的问题。笛卡尔通过物理学,在物质世界之中发现一种恒定不变的运动规律,这些规律是永恒真理。但在斯宾诺莎看来,在思维的属性中,存在着一种理解,能够理解“宇宙的总体性的一面”,但这种理解原本只属于神,但人的理性能够以某种方式分有这种思维的无限性(神),即所谓的“在永恒的面目下”来观看和思考。
对于有限的人而言,人作为有限的身体,身体作为物质世界中的一部分,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其他的物体,或者说依赖于其他物体而存在。对于无限的样式,其存在和其本质是同一的。而对于有限样式,其存在和本质是不同的,其存在依赖于其他的一些物体,从而受限于有限的存在,外在于其原因。因此,有限样式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匮乏。人的身体,是一个机器,由许多其他机器构成的复杂的机器。而灵魂,斯宾诺莎定义为“灵魂是身体的观念”。这说的并不是灵魂是一个关于身体的图像,而是指的是,在思维的属性之中,对于“我”的一种定位、一种肯定、一种限制。在广延中,身体是一种定位,一种限制;在思维中,灵魂是一种定位。
灵魂作为一种有限的样式,就推出两种观念,一是关于灵魂自身的观念,二是关于身体的观念。关于外在物体的观念是不相合的(inadéquate),即使观念与观念对应的物体并不一致。当且仅当一个观念的原因为我们所认识时,这个观念才是相合的。因此,对于一切有限样式的观念,都是不相合的,因为有限样式的原因不在其自身,而在自身之外。
灵魂对于灵魂自身的观念,也是不相合的,因为灵魂本身的原因也在自身之外;对于物体、身体的观念,也是不相合的;我们认识到外部物体,是当外部物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印象;外感官(对外部的感知)更多地依赖于我们的身体的性质,而不是外部事物的性质;因此,即使在外部事物并不存在时,我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心灵能力唤起关于外部事物的形象,这就是回忆或者想象。就此而言,我们关于自身,关于外部事物的知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相合的,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极难获得真正的知识和真理。
因此,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依赖于一种我们无法全部理解的自然进程;自然是不透明的、不可理知的。因此,有限的存在,即是在时延(duree)中的存在,也是无法理解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在有限样式之中,找到原因来解释我们自身的存在。但是,斯宾诺莎还将证明,在这个有限的存在之中,将诞生某种理性。他已经证明,在自然之中,我们只能获得混乱的、不清晰的观念。
但是,笛卡尔向我们揭示出,存在着一些绝对的真理,这些真理,以其自身之昭昭,向我们显示其自身。有一个相合的观念,在每一种样式之中都将得以呈现,这就是关于上帝的观念;此外,我们还可以获得关于共同概念的观念。这些共同概念和上帝观念的总和,就构成了理性。由此,我们形成了三种认识方式:第一,经验的,是由关于有限样式的种种不相合的观念构成的;第二,理性的,由共同概念构成,可以进而获得种种推论;第三,直观,直接洞察上帝的观念,以及基于上帝的诸多共同概念。
在斯氏看来,人要么屈从于错误,要么走向真理,没有第三条路。
人的激情与奴役
人就其本质而言,是倾向于犯错的。人要么遭受,要么主动。当其感受到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的原因是在自身之外,就是遭受;相反,如果他自身是其情感的原因,他就是主动者。在自然进程之中,有限的身体和有限的灵魂,源源不断地遭受着,形成在外部压迫于不得不产生的情感和观念。但人也可以主动,当其具有相合的观念,当其是其情感的原因。
不相合的观念,如何在我们心灵之中产生各种激情(如快乐、痛苦)。“一切存在都倾向于保存自身”。因为一切存在都是对于神圣的一种表述。这种不断保存自身,成为自身的努力,就是努力(conatus):在身体中,这种努力就是欲望(appetitus),欲望是人的本质;在灵魂之中,这种努力就是贪念(cupiditas)。观念不只是图象,而且也是自身的定位(position de soi)。努力不同于对于善的追求;然而,努力却是一切可能的情感的原则或者基础,即一切存在无不努力追求自身的保存,无不努力追求自身存在的扩大;外在的原因,或者是有利于我们保存自身的存在,或者不利于;由此产生了两种基本的情感,快乐和痛苦。
快乐,就是身体的完美性的增加;而痛苦,就是身体的完美性的减少。爱,就是在快乐的观念之上,增加了关于作为快乐原因事物的观念,如:我快乐,之所以快乐的原因是A,因此,我爱A。恨,则是在痛苦的观念的基础上,增加了痛苦原因的事物的观念。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出各种不同的情感。一切情感或激情(passion),皆是出自于三种最原始、最基本的情感:欲望、快乐、痛苦。三种基本情感的不同组合,以及观念和想象的种种加成和改装,形成了人类形形色色的、复杂无比的情感。例如,同悲(commiseration),就是感受到同类感受到的痛苦。
自由与永恒生命
人并不完全被自然进程所限定。当其具有相合的观念、真观念,人就变为主动,变成理性的行动者。例如快乐这一情感,当其为不相合的观念所引起时,是一种激情;当其是相合的观念引发时,则是一种主动。欲望也可以是激情,也可以是主动。只有痛苦,以及基于痛苦的各种情感,只能从属于激情。
德性行为,在于受到相合观念的引导,或者追随理性。人如果追随不相合的观念,人与人之间就会不同,就会引发冲突。人如果追随理性,追随共同概念,那么因为理性是同一的,共同概念就是一些所有人都能够通过理性发现、认识、赞同的概念,这样人与人就会取得一致。因此,社会和政治,就在于这种求同去异。
一切激情,就其倾向于保存我们自身而言,是善的。理性的标志,就是努力去理解,这种努力最终是与努力(conatus,努力保存自身之存在)是一致的。从而理解到,一切情感之中,都有某种与努力(conatus)一致之处。从而在通过对我们内在的主动能力(行动能力、行动潜能)的直观之中,达到一种内在的和平。
有智慧的人的内在和平,不在于对于某种自由意志的依赖。在笛卡尔看来,人具有某种自由意志,从而可以在身心之间达到某种平衡。然而,在斯宾诺莎看来,需要通过一种持续的方法,通过理解,使得这些情感,不再是激情,而是转变为德性行动。这里所涉及到的,是一种心性的转换,一个化被动为主动、化情感为理性的过程。
这种转换是必需的。因为自然的进程,使我们处在激情之中,处在与他人的冲突之中,处在错误之中。通过理性,我们知道,我们的快乐和痛苦都不过只是自然进程的一种效果,我们就停止原有的爱和恨,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爱和所恨的并不是快乐和痛苦的真正原因之所在。战胜一种激情,就是认识这种激情,形成关于这一情感的真正的相合的观念。这种认识,使得我们获得一种真观念,认识到我们自身存在的完美性;从而这种认识伴随着以快乐;这种快乐使我们关联到使我们作为有限之样式得以可能的真正原因,即神。这种认识也就伴随着理性,伴随着对神的爱。
对于共同概念的使用,使得人成为其激情的主人。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体,其存在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神。关于一切事物,关于自身,我们会形成一种新的看法。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被自然进程所规定。但我们也认识到,在我们的个体性之中,有着某种绝对肯定性的东西。我们不是把个体附加在宇宙之上,而是认识到我们的个体就是宇宙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我们作为个体与宇宙的其他部分有着某种共同性。通过第三种认识,我们直接地把握到我们的个体性必然地依赖于神,如同我们把握到算术和几何真理。
这样,人们就上升到永恒的、不依赖于任何时延的生命。永恒生命,并不是身体死后,灵魂的继续存在,也不是灵魂不朽。通过第一种认识,人被把握为有限的、个别的存在;通过第二种认识,人被视作融入到必然性的宇宙之中;通过第三种认识,人再次被呈现为个别的存在,但却是永恒的存在。也就是说,通过第三种认识,人得以从有限过渡到无限,从时延过渡到永恒。
如何从时延到永恒?首先开始于第二种认识,通过知性和共同概念来认识。这样使用理性,已经把握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在斯宾诺莎这里,精神生活并不是一种返归(乡愁式的归家),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进展。通过知性和共同概念,我们把握到了心灵中的某种肯定的、永恒的东西。人的本质,或者说理性的本质就在于这种原初的肯定性的东西。而永恒生命,就在于从其源头出发,对这种本质的内在发展。通过第三种认识达到的快乐和对神的爱,是绝对肯定的东西,全然没有任何否定的、黑暗的一面,是绝对的光明。而这种绝对的肯定,与努力(conatus)最终是一致的。因为这种努力(conatus),构成了存在的本质,是一种纯粹的肯定,把存在设定为不受任何时延的限制,也就是让存在上升到永恒,而正是在这种永恒之中,人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