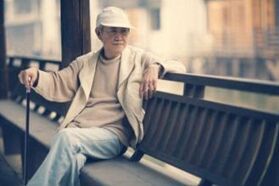
转自:王老 本文大量借鉴了木心作品《鱼丽之宴》
我所有的都是常识而已
浅浅的知识比无知更使人不安,深深的知识使人安定,我们无非是落在这样的一片浅浅深深之中。
人类文化经历了充满神话寓言的童年,文艺复兴情窦初开的少年,浪漫主义狂歌痛苦的青年,杰出的艺术各以其足够的自知之明为其所生息的时代留下了不可更替的特征。童年幼年是热中,少年青年是热情,而壮年中年是热诚。
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立志,自认为练达,自认为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少年时最憎恶的那种人。
人贵,有自知之明;人贱,就没有。
有趣,是一辈子的春药;自我感觉良好的“有趣”,是人生的毒药。
“生命”是由“好奇心”、“求知欲”、“审美力”掺和蛋白质之类构成的。
书本告诉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是我最向往的,我知道不看点更大的,此生必然休矣。
宇宙是不与人对话的
人的自知之明,从狂热的宗教信仰终于冷却为宇宙论。
福楼拜说:“唯物唯心,都是出言不逊。”我就接说:“有神论无神论,都是用词不当。”
宗教事小,信仰事大。我信仰“信仰”。
假使不通过宗教,人类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去触及宇宙本体?如何与宇宙对话?
“理”的探索,“智”的推论,“灵”的体识。
宇宙是不与人对话的,人类始终只能独白。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三个哈姆雷特在一个戏台上同时独白。
三个哈姆雷特的独白,第一个咬字清晰,第二个条理分明,第三个声调优美。
科学家能做的是对“存在”的解析,是不具“创造”性的。
史学使人清醒,哲学使人坚定
历史这种东西,即使短短一段,也充满寂寂的笑声,多少人还想以“行过”算做“完成”。
痴心而明哲,明哲而痴心。唯其痴心,再不明哲就要烧焦了,因为明哲,没有这点痴心岂不冻死在雪山上。
迷路,并无小路大路短路长路之区别。不能说在大路长路上迷路就不是迷路了。走在达不到目的的路上,就是迷路。
一个人,受另一个人的影响,……是分时期的,如果终身受一个人的影响,影响到了可以称为最大——那是误解,至少是病态。
纪德说:爱“爱”,不爱单个的人。
歌德说:假如我爱你,与你何涉。
未来的计划、行程如何?
不止一次地周游世界,日日夜夜地写,也要画,最终目的是告别艺术,隐居,就像偿清了债务之后还有余资一样地快乐。
世界是整个儿的,历史是一连串的,文学所触及的就是整个儿的世界和一连串的历史。有点,有线,然而如果是孤立的点,断掉的线,经不起风吹雨打。故意触及,是个人性的,必然触及,是世界性的;表面触及,是暂时性的,底层触及,是历史性的。
唯有平常的事物才有深意,除此,那是奥妙、神秘。奥妙神秘,是我自己的无知,唯有奥妙神秘因我的知识而转为平常时,才从而得到了它们的深意。
畅销书是行过,经典著作是完成。凡是令我倾心的书,都分不清是我在理解它呢还是它在理解我。
繁华不堪的大都会的纯然僻静处,窗户全开,爽朗的微风相继吹来,市声隐隐沸动,犹如深山松涛……电话响了,是陌生人拨错号码,断而复续的思考,反而若有所思。
我觉得人只有一生是很寒伧的,如果能二生三生同时进行那该多好,于是兴起“分身”“化身”的欲望,便以写小说来满足这种欲望。
粉墨是人事,场是天命
以粉墨登场而换来的知名度是“行过”,洗尽铅华至心朝礼于艺术才有望于“完成”,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青春,理应是迷离惝恍的,在追思中却显得水清见底,那“底”,都分别超越了个人性,像碎镜子中的纷纭世界,一片一世界,加起来,通常就把它们叫做“时代”。
童年的我之所以羡慕画家,其心理起因,实在不是爱艺术而是一味虚荣,非名利上的虚荣,乃道具服装风度上的兴趣的虚荣,因此仍可还原为最低层次的爱美。
学生时期最宝贵的是“无忧无虑的心情”,青春都具有不知从哪里来的“锦绣前程”的保证,谁都是天才、准天才,天才的偌大的萌芽。
一切崩溃殆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绝望中求永生。
要脱尽名利心,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有名有利,然后弃之如敝屣。
木心(1927-2011),原籍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画家,在台湾和纽约华人圈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和传奇人物。出版多部著作。在“文革”囚禁期间,用白纸画了钢琴的琴键,无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陈丹青说,“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 著有《哥伦比亚的倒影》、《琼美卡随想录》、《温莎墓园日记》、《即兴判断》、《西班牙三棵树》、《素履之往》、《我纷纷的情欲》、《鱼丽之宴》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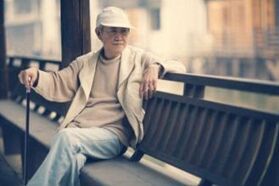
木心说:“贝聿铭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因为实话,尤甚于反讽——50年代末,他躲在家偷学意识流写作;60年代“文革”前夕,他与人彻夜谈论叶慈、艾略特、斯宾格勒、普鲁斯特、阿赫玛托娃;70年代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书写文学手稿,令人惊怵不已;80年代末,他年逾花甲,生存焦虑远甚于流落异国的壮年人,可他讲了五年文学课……《文学回忆录》这本书,布满木心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他有些事看得很透:“不要名不要利,是强者,而多半是无能的弱者,我不取‘陶潜模式’,宁择‘王维路线’……”木心常说自己是左手画画,右手写文章。也许在他看来,绘画水平终有一日会盖过文学成就,才发出“文学既出,绘画随之,到了你们热衷于我的绘画时,请别忘了我的文学”这样的感慨。
《鱼丽之宴》简介:
《鱼丽之宴》是木心关于文学的答问录。“鱼丽”这两个字,原来是见之于诗经中的,见于小雅。鱼丽于罶,鱼丽于罶,鱼丽于罶……一再重复出现,仿佛音乐也是这样,重复起来,低回几次,始有一种气氛。丽是落入的意思,罶是一种渔具。鱼丽之宴无非是说鱼很丰盛的宴席吧。一个人被记者逼住来做访谈,多少有些“鱼丽于罶”的意思。一般老老实实的招供是一种,但木心的不那么老实,水紧鱼跳,水不紧,他的鱼也喜欢跳。他的思绪和情绪,常常是吉光片羽的闪烁。 -深圳特区报 王绍培
——我曾见过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年轻,真像是一个理由,一个实际上毫无用处的理由。
——浅浅的知识比无知更使人栗六不安,深深的知识使人安定,我们无非是落在这样的一片浅浅深深之中。
——中国的历史是和人文交织浸润的长卷大幅,西方的智者乘船过长江三峡,为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饱涵人文精神而惊叹不止。中国文化发源于西北,物换星移地往东南流,流到江浙就停滞了,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辩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西方人善舞蹈,中国人精书法,中国的「书法」之道,是所有的艺术表现手段中,最彰显天才和功力的一种灵智行为。
——当听到纪德说“爱爱,不爱单个的人“——我已吃了一惊。以为他窃听了我内心的自白。当歌德说”假如我爱你,与你何涉。”——我太息,以为能做到的只有这一步,而这一步又是极难做到的......
——我走过的路,不是信仰的路程,沿途所见的是一代代宗教家都背离起始祖意旨,虚伪敷衍,曲解夸大,甚而作恶多端。
——海峡一岸是自绝于传统文化,曲解了世界文化,海峡另一岸是曲解了传统文化,自绝于世界文化——文化断层必然是连带风俗习惯人情世故一起断掉的,所以万劫不复。这一征象倒真是中国特色,别的文化古国不致断得如此厉毒酷烈,肇因是海峡两岸各有其意识形态,而相同的一点是价值判断的混乱,混乱的结果是价值判断之死亡,无所谓价值,不需要判断,浑浑噩噩的咬牙切齿,捕风捉影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在绝望中求永生。”常见人驱使自己的“少年”“青年”归化于自己的“老年”。我的“老年”“青年”却听命于我的“少年”。顺理可以成章,那么逆理更可以成章——少年时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足够我受用终生。
——这是一种舛戾的风气,怎么都顺手牵羊般地借一句唐诗来作文章文集的题名,古人是绝不会这样没自尊的,"五四"时期未见有无聊如此者,弄雅成俗何其酸腐惫赖,诚不知谁是始作俑者。
——以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少小的我已感知传统的文化,在都市在乡村在我家男仆的白壁题诗中缓缓地流,外婆精通《周易》,祖母为我讲《大乘五蕴论》,这里,那里,总会遇到真心爱读书的人,谈起来,卓有见地,品味纯贞,但不烦写作,了无理想,何必计划,一味清雄雅健,顾盼晔然,晏如也。你若约他一同去买书,步行二十里不出怨言。读到了杰作,谈一个通宵略无倦容--这类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代代辈出,到处都有,所以爱默生也会觉察到这个伟大的"潜流"之存在,他说说又没说下去,爱默生总是这样,其实还可以说下去:如果有一时期,降生了几个文学天才,很大很大的,"潜流"冒上来扈拥着"天才",那成了什么呢,那便是"文艺复兴",或称文学的"盛世","黄金时代"。
——史学使人清醒。哲学使人坚定。
——我的画已经全部毁灭,也预知今后画出来的东西很难幸存。画之前、画之中、画之后,三重快乐是分内的。塞尚他们所烦恼的是要取得第四重母爱的快乐。延种本能在精神上竟也这样亢强,以致使那些才智过人的艺术家偏执到如此焦躁的地步。为了免于这第四重快乐,我曾一度成为文化形态学的赞赏者。
——木心《鱼丽之宴》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