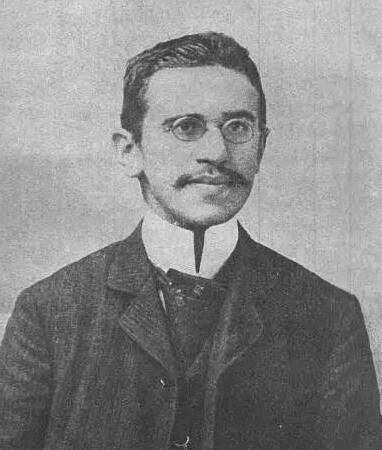
我不能理解我的罪孽,因为我仍然罪孽深重
I cannot understand my iniquity, for I am still sinful
作者:魏宁格 发布时间:2017-6-7
魏宁格 | 我不能理解我的罪孽,因为我仍然罪孽深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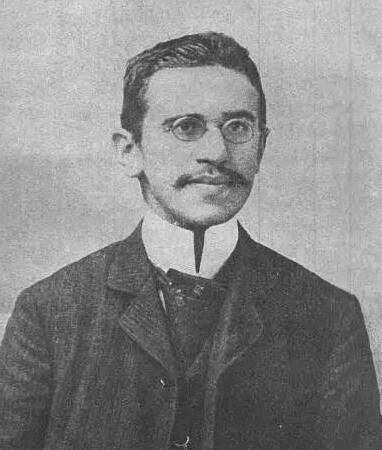
我面临着三种可能:绞架、自杀,
或者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辉煌。
▼
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如果意外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失声尖叫,那一定意味着,
她担心那样子不够好看。
▼
女人的端庄正是一种假正经,
即夸张地否认她天生的不正派。
▼
我不能理解罪孽,只因我身在其中。
理解之时,已是跳出圈外之时。
我不能理解我的罪孽,因为我仍然罪孽深重。
▼
许多没有子女的婚姻都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
逻辑和伦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他们不是别的,而正是对自我的责任。
魏宁格,这位早逝的哲学天才,23岁便举枪自杀。
魏宁格一生只有两部作品。21岁,他便写出了令他跻身现代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领域各种大师之间的作品《性与性格》,这在整个哲学史是绝无仅有的。他自杀之后,其友人整理并发表了他的遗作,格言式随笔集《最后的事物》。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思潮可以窥见他的影子,在维特根斯坦、卡内蒂、弗洛伊德、布洛赫、卡夫卡、劳伦斯和乔伊斯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响。
然而,他悖论式的格言体言论,对两性心理、同性恋、施虐受虐、犹太文化以及女性等主题惊世骇俗的见解,使得他被视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反对妇女解放者和排犹分子。
初读魏宁格,许多人会觉得他和叔本华、尼采一样对女性充满了偏见与憎恶,就连弗洛伊德在看了他的手稿之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天才无疑,但性心理错乱,其憎恶女性和犹太人是“阉割情结”的表现。
1880年4月3日,奥托-魏宁格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手艺人家庭。少年时代起,就在自然科学、数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显示了早熟的才能,其语言天才尤其突出,除了自己的母语德语之外,他还精通西班牙语、挪威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16岁时还曾打算发表一篇词源学论文,内容是研究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语形容词。
1898年,18岁的魏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研习哲学。
1901年,21岁的魏宁格将《性与性格》的草稿交给了弗洛伊德,希望弗洛伊德看了之后能够推荐发表,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引起重视。半年后,魏宁格把《性与性格》作为学位论文交给维也纳大学,其第一部分使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同一天,魏宁格正式皈依基督教,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1903年,《性与性格》出版后,魏宁格曾说——“我面临着三种可能:绞架、自杀,或者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辉煌。”同年10月4日,23岁的魏宁格因苦闷绝望,举枪自杀于维也纳的贝多芬故居里。不久之后,魏宁格的《性与性格》成为畅销书,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一个文化事件。
自杀者几乎都是施虐狂
神秘主义者(无论波伊姆之类的见神论者,还是康德之类的理性论者)属于受虐狂,非神秘主义者属于施虐狂;北欧国民(还有犹太人)是受虐狂,而南欧国民为施虐狂,德国人和希腊人则二者兼有,但受虐狂居多;威尼斯箴言诗、赫曼和多罗西亚是施虐型,伊菲姬尼、塔索、维特、浮士德(基本上,格雷琴插曲部分例外)等为受虐型。《奥德赛》的作者是施虐狂,只有女妖喀耳刻是理想的受虐狂(理想型受虐狂不与受虐抗争,而是面对具体事物保持被动)。埃斯库罗斯、理查德·瓦格纳、但丁,尤其是贝多芬和舒曼是受虐狂,威尔第(还有马斯卡尼和比才)更多为施虐狂,所有阿纳克里翁派诗人和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同样如此,提香、保罗·委罗内塞、鲁本斯、拉斐尔、莎士比亚等也具有很多施虐特征,但是基本属于受虐型,在女人面前,不能像歌德、但丁、易卜生和理查德·瓦格纳那样,清晰地区分性与爱。《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一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受虐狂形象,《汤豪舍》《黎恩济》和《荷兰人》次之。
[几何学对应于和谐,算术对应于节奏(时间单位相加?),此为前面注释的解释。]
实施孤立且重大个案的罪犯为施虐狂,而不屑于孤立个案的大手笔罪犯则为受虐狂。拿破仑是受虐狂,并非人们所以为那样的表面,他与约瑟芬的关系、对维特的痴迷、对待天文和上帝的态度等,即是证明。具体的女人从未占据他的心。
另外,施虐狂完全可以是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
如果现实的女人过于强大,施虐狂也许会求助于强奸杀人,(?)不一定是如左拉那样的报复行为。
英国人总体上属于受虐狂,他们的女人也许正因此而严重扭曲,失去女人味。
拿破仑对他的士兵说:“Du haut de ces pyra-mides quarante siècles vous contemplent”(四千年从这些金字塔俯视你们),其中隐含着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为真正的法国人和施虐狂所不能企及。
引人注目的东西,对受虐狂而言是事物的相似性,而对于施虐狂而言则是事物的不同。
时钟、日历对孩童时代的受虐狂而言,构成极大的不解谜团,因为时间永远是他的主要问题。
如果当前蕴含着比过去更多的真实性,那么,受虐狂从来不能轻而易举地超越过去,而施虐狂却总能那样。
受虐狂认为一切都是命运安排,而施虐狂则喜欢把玩命运。尤其是在具体的痛苦之中,受虐狂总是会产生命运的念头,在他看来,该痛苦只具有涉及此念头的真实性。所以,施虐狂就是女人的命运,而女人又是受虐狂的命运。“女人”属于施虐型(属于女人感受中积极的一方),“夫人”属于受虐型。
施虐狂与受虐狂的关系,就是当前与永恒的关系。当前是人们权力的唯一对象。谁对权力游刃有余,就能够利用它,如施虐狂那样;谁感受不到权力的真实性而苦不堪言,就会试图把它视为永久的目标而唤醒它。二者在道德追求方面的特点也是如此:一个希望把一切永恒变为当前,另一个则希望把当前全部变为永恒。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空间。施虐狂相信并且希望今世的幸福:他是“富人区”“无忧宫”的男人,而受虐狂则需要一个天国。
施虐狂因悔过而怪罪自己,认为悔过就是软弱(Carpediem!),而受虐狂满脑子都是它的威严(卡莱尔)。
自杀者几乎都是施虐狂,因为他希望独自摆脱当前,为所欲为;而受虐狂则必须首先垂问所有永恒是否允许和必须自杀。
施虐狂希望(违背他们的意愿和秉性)帮助人们达到(瞬间的)幸福或者痛苦:他知恩图报或者报复成性。
感激和报复之中永远包含着对(超越时间的)他人的冷漠和残忍,与所有不道德行为一样,二者都是越轨,也就是说,与他人的功利性交往。
心理的羞愧感,即连续性,不轻易从自我中舍弃具体的内容(参见《性与性格》第一版436页),属于受虐型。
当今的医疗保健和诊断治疗很不道德,因而也不成功:它追求由外及内,而非由内及外的效果,与罪犯的纹身无异,即从外部着手来改变自己的外表,不追求思想的改变。这样,他本质上也否定自己的外表,所以没有勇气目视镜中的自己,因为他(理性的人)仇恨自己,没有爱自己的欲望。如果有别人冒犯,罪犯会很高兴(如同他每次与别人的接触,对别人施加影响,给别人造成不安一样惬意)。
每一种疾病都有心理诱因,必须由病人自己通过他的意愿才能治愈:他必须自我努力从内心认识疾病。所以疾病都只是无意识形成的“进入肉体的”精神,所以,当它上升为意识,疾病就治愈了。
一般而言,罪犯不会生病,他的原罪与众不同。浅显地想象,情形大致如此:罪犯在原罪形成的瞬间背弃上帝,从天国坠落尘世,然而,对立足之点却全神贯注;另一个有病之身(神经衰弱者,神经错乱者)坠落大地时,恳切地抬头仰望着上帝,平躺落地,但是对此意识全无,神情涣散。假如把后者的危险比作植物,前者的危险比作动物,那么,事情十分合拍:植物由地心垂直生长直奔天国,动物的目光则俯向大地。(与动物不同,植物永远不能成为不道德的象征。)
每个人永远只能把自己理解为质量,只有通过与别人的比较,才能补充以量的观察。数量和时间。
优秀音乐家的音乐首先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历史和社会:共处于一个空间的人们总是组成一个相对于新来者的共同体。
感恩和复仇别无二致:同属二者的是一种瞬间的真实感受:心怀感恩和复仇成性的是施虐狂,不是受虐狂。
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如果意外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失声尖叫,那一定意味着,她担心那样子不够好看。
不协调是音乐不幸的瞬间,恰恰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有这样不幸的刺耳之音,并因而成为画蛇添足之笔。
优秀的格言家一定充满仇恨。
居然有人相信,献身于多神就可以摆脱一神。
固执狂经常把固执和毅力混为一谈,没有什么更甚于此。
与心理学家截然不同,数学家是一个非常简单之人,简单得犹如一个空间。